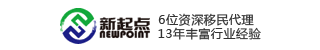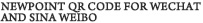澳洲史上最震撼逆袭!这个流浪汉,最后当上了大学教授
没有人喜欢流浪汉。
虽然我心里也清楚,每一个流浪汉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;我也曾暗暗幻想过,说不定从超市买只烤鸡丢给他们还能换来几招降龙十八掌,但从来也没敢跟他们搭过话。
他们总是那样头发油腻、胡子拉匝、衣裤邋遢,看上去很可怜,更重要的是可怖——一副光脚不怕穿鞋的样子,万一暴起伤人怎么办?
前几个月,从大学生走到了公务员、再从公务员走到了流浪汉的沈巍曾掀起网络热议,被誉为“流浪大师”。
在澳洲,却曾有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,从流浪汉走到了野人、再从野人走到了……教授。
格里高利·史密斯(Gregory Smith)现在是南十字星大学的教授,但多年以前,他就曾经是我们在街头避之不及的流浪汉,甚至是传说中神秘莫测的神农架野人。
1.父亲的拳头
格里高利出生在新州北部的小镇塔姆沃思(Tamworth),这里是澳洲的乡村音乐之都,据说连宠物都会弹吉他……
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个地方还没有这么文艺。
这里的人做得最文艺的事情可能就是喝酒,就像小格里高利的父亲一样。
他小时候一直想不明白父亲身上的味道为什么这么难闻,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酒味。
而他父亲平生有两大爱好,一件是喝醉了酒打老婆,还有一件是喝醉了酒打孩子。
母亲可能对这样的暴力也已经麻木,当五个孩子遭到毒手的时候,她从来都是熟视无睹。
所以格里高利从小对暴力就产生了间谍般的敏感。
他尽可能地坐在门窗旁边,随时准备纵身出逃;尽可能地把扫帚放在身旁,随时准备骑扫帚飞走……当然不是,是随时用来抵挡攻击。
直到现在,每当他走进一个新的处所,他都会机警地快速扫描房屋结构、地形通道,每一个附加的紧急逃生出口都能够让他如释重负。
这样如履薄冰般的噩梦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0岁,然后他开始了一场新的噩梦。
2.修女的恩典
1965年,母亲把孩子都送到了塔姆沃思北部小镇阿米代尔的一个孤儿院。当时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,直到多年以后才醒悟:原来母亲是不要他们了。
在这个教会管理的孤儿院,他的生活突然变成了每天做弥撒、唱队歌、背核心价值观、以及其他各种宗教仪式,让他一点都摸不着头脑。
迷茫也就罢了,随之而来的是羞辱。
每天当男孩们的玩耍时间结束后,他们都要上楼被洗澡——被大他们三四岁的女孩洗澡。
他们排好队,一个个走到女孩面前,脱光衣裤走进浴缸,让女孩帮他们擦洗身体,在女孩们的嬉笑声中无地自容。
有一个叫贝丝的女孩,甚至连续好几个月对他进行了性侵犯。
修女的詈骂、责打更是家常便饭。
但打骂对犟头犟脑死不悔改的他毫无用处,于是他经常被送到一个逼仄的小黑屋里,一个人呆在里面闭门思过七八个小时。
有一天,他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,一溜烟跑出了孤儿院。
那是一个烤箱般的夏天,他一路狂奔,跑到干渴难耐时,就喝地上的泥水,一直跑到被警察逮住。
警察把他狠揍了一顿,说他是个不识好歹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,让苦心养育他的修女操碎了心——她们都是为你好知不知道?然后把他送回修女那里继续关禁闭。
在小黑屋里,他开始学会闭上眼睛,像破碎者布兰一样灵魂出窍,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,那里有树林,有田野,有岩洞,有动物,有WIFI……但最重要的是——不能有人。
3.专家的诊断
一年半以后,母亲终究还是把他接回了家,那个其实他也一直想要逃离的家。
这十几年里,他眼中的人际关系似乎只有两种:要么是你胖揍我一顿,要么是我胖揍你一顿。
而弱小如他,似乎总是被揍的那一个。
在学校里怯懦、孤僻的他,引来了许多嘲笑和霸凌,而嘲笑和霸凌更加深了他的怯懦和孤僻,以及难以名状的愤怒。他打架、偷盗,是青少年劳教中心的常客。
14岁的时候,他被带到一个心理专家那里。
专家问了他几个问题,但是他对这些问题茫然不解,只是呆呆地望着对方,一声不吭,就像一头鸭子静静地听着鸡在讲话一样。
于是专家的诊断结论是: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者(Sociopath)。
这个“馊朽葩死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?他不懂,却觉得这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,因为自己终于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标签了,还是专家意见!
那怎么样才能活出“馊朽葩死”的人样来呢?他费了好大的劲了解到,“馊朽葩死”不喜交际,仇视社会,热衷于制造麻烦,尤其是用暴力的方式。
他想,嗯,这有何难,不都是我擅长的么?
手持“馊朽葩死”的资格证书,他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酗酒、吸毒、斗殴了。那时候只要有人多看了他几眼,他就会冲上去拳脚相加打到残血,就像一颗可以用眼神引爆的定时炸弹。
4.最大的缺点
19岁,他从劳教中心出来,正式踏上他所要“反”的那个社会。
偶尔他也会温良恭俭让地抽风一阵子,他的前妻就是被这暂时的假象蒙蔽了,卷入了三个星期的家暴之中,“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”是注定的结局。
他后来才意识到,自己已经活脱脱变成了他父亲的样子。
他的工作也像他的婚姻一样,只是一段段风萍聚散的露水姻缘,如漆似胶的结合总是在莫名袭来的怒火中燃烧破裂。
他还曾有声有色地做过一个清洁生意,雇了好几个人,赚了不少钱。
所以他很有爱地邀请当地的流浪汉住在他所租的办公场所,免费吃鸡,尽情嗑药。
有一次回家,他发现这些客人把房子搞得像猪窝一样,就威胁说:下次再这样,我就一把火烧了这房子!
当数周之后这些客人旧疾重犯的时候,他暴露出了身上最大的缺点:说话算话。
他给了那些人10分钟清场,然后提了一桶汽油就把房子点着了。
于是,二十多岁的时候,别人的家庭事业才刚刚萌芽,他的家庭事业却已经提前终结了。
他被法庭判定有精神疾病,逃过了纵火罪的惩罚,从此开始在澳洲东海岸漫无目的地游荡。
他睡过公园,醒来却发现已被草坪自动喷淋;他睡过海滩,醒来却发现已被打得遍体鳞伤。
生活留给他的选择似乎已经不多了。
直到有一天,他来到新州北部的一片雨林,突然想起了儿时在小黑屋中梦想过的那片无人之境,心里一个声音对他说:何不留下?
于是他就一个人霸占了这片森林,一霸就是十年。
5.爬来的宵夜
当他踏入森林的时候,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包烟、一盒火柴、几件衣服和一件雨衣。
一开始,他在一块大岩石上用几根木头支起了雨衣,在这样一顶简陋的帐篷了住了几个星期。
佛系如他本以为可以如此将就下去,但一些不请自来的过客不时地把睡梦中的他当作爬行的山丘。
一天晚上,他感觉到一条冰冷滑腻的物事贴着他的胸脯缓缓游过,他屏住呼吸直到那物完全离开他的身体,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一条五英尺半长的蟒蛇,他一下子斗神附体,扑上去毫不客气地把它当成了宵夜,以及此后接连几日的三餐。
不过各种水蛭、蠕虫也纷至沓来,不堪其扰的他把家搬到了高处。
他慢慢经营住所,堆积木材,让篝火保持不灭;却尽量控制烟雾,以免被森林外的人类察觉踪迹。
每天清晨,他总是从群鸟绵密的交响乐中醒来,听一阵子就出发觅食。
上次吃了蛇肉以后,他夜复一夜地做起了女娲索命的噩梦。
一朝咬了蛇,十年怕井绳,所以再也没敢去打蛇的主意。
他开始猎取森林里可以找到的各种奇怪动物,蠕虫、蝙蝠、蜥蜴等等,生啃熟咬两相宜。
旧瘾难戒,他空闲下来就在森林里辟了一块金三角,种起了大麻。他把收获的大麻和剥下的动物皮拿到森林边上的村庄去,换取大米、面粉等食物。
有一次他突发奇想,买了一个垃圾桶、一些酵母和糖,回到森林里开始酿制啤酒。成品的味道冲得像马尿,但是对一个森林里的酒鬼来说,就像是男生宿舍出现一头母猪一样。
他生产的农副产品越来越多,渐渐跟森林周围的村庄之间编成了一张原始的交易网络,居民们也对这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神出鬼没的存在渐渐习以为常。
有一天,他收到一张纸条:花径不曾缘客扫,蓬门今始为君开,我在马路那头第一扇门等你。
他过去一看,原来是请他住进一辆房式拖车。丫的,老子一言既出、十二个气缸也难追,说好的隐居,难道是开玩笑的么?不去!
几年以后,他跟附近的村民谈起这件事,才知道那个邀请者的目的,并不是出于对他的仰慕,或者觊觎他的什么武功秘籍,而是想找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野人在门口驻守,让入侵者闻风丧胆......
6.学霸的诱惑
十年下来,由于饮食结构的失衡,以及长期以来酒精和大麻对神经的麻痹,他已经瘦弱得不成人形,需要撑着拐杖才能行走。
长年闭塞不通人言,也使他的大脑出现了一些奇异的变化,自动升级成了一个智能信息订阅系统,眼前时不时浮现出鬼怪神灵的表情包,有一些还自称是他的祖先,不定期地向他推送往事如烟、人生苦短之类的鸡汤。
有一个订阅号只是重复发送同一条语音消息:你本无过,何必自责?从今而后,活出自我。
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洗脑式的连续滚动播放:行吧,你赢了,我就再给这个社会一次机会!
走出森林以后,他到医院就诊。医生立即被他的款型圈粉,也不管他是不是报得出Medicare号码,只管实施治疗直到他恢复了健康和神志。
出院那天,他坐在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,凝视着天地间除肉身之外一无所有的自己,之前混乱模糊的45年人生慢慢清晰起来。总结起来就是:他永远怒气冲天,却不知怒从何来;他随时准备战斗,四围却空无一人。
浓雾散尽,他终于看清楚了那个一直以来与他挣扎缠斗不休的人,原来只是他自己。
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,争斗之心尽去,撕逼之欲全消。
但作为一个森林里出来的新移民,他遇到了跟华人同胞一样的问题——找不到工作。
除了酿啤酒、抓蝙蝠,他没有任何技能。
于是,他向TAFE申请了免费的计算机课程。
六星期的课程学下来,他的感受体现了典型的“反社会人格”,跟常人完全相反:我讨厌电脑,但是我享受学习。
而TAFE的老师告诉他,如果他想的话,可以继续深造读大学,于是他又读了大学,专攻社会学。
再后来,他发现自己拿学位拿上瘾了,打怪升级根本停不下来,一直到修完了博士学位,成为了史密斯教授。
在大学里,他依旧无家可归,依靠着政府的救济金渡日,慢慢攒了点钱,买了一辆旧货车,睡在车里面。
读完本科的时候,南十字星大学打电话给他,请他去做讲师。
他终于有了足够的经济来源,像正常人一样过上了房奴的生活。
他的硕士研究项目是关于孤儿院的孩子,深深解剖那些跟他一样因恐惧而把往事深藏心底不敢声张的人们,以及背后的腐朽体制和扭曲人性。
他还找到了当年那张“馊朽葩死”的诊断书,把它带到办公室,挂在自己学位证书的旁边,遥相辉映,相得益彰。
最后,
那个曾经遗弃他的社会,如今却重金聘请他来关怀那些因“反社会”而被遗弃的孩子,对社会的这种一半在始乱终弃、一般在拨乱反正的对消与循环,还有谁比他更能洞悉其中的荒谬呢?
PS:本文改编自ABC的Conversations节目Gregory Smith's re-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(点击阅读原文收听)和Australian Story节目Out of the Woods,图片来自网络。